净土今说
张澄基 著
(一)感言
这是佛学今诠的最后一章了,回忆几年前在写上册时,自己曾想,除了大小乘的基本教义外,还应讨论一些大乘的主要宗派,如唯识、中观、禅宗和密宗等。但经过几番严重的疾病,这个残体已不容许我这样去做了。在写毕般若之后,本书原可收场,但想来想去还是不能不说几句关于净土宗的话,因为净土宗在中国佛教中,可算是一个最普及、最实用亦最具影响力的宗派了。净土宗的道理似浅实深,其行持似显实密,其成果似迟缓实疾速;其目的虽像是死后往生的自利,其作用却是现享法乐和济世益人的二利庄严。中国净土宗的历史有力的证实了这几点。但在讨论净土以前,我有几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写这篇“净土今说”,感情的成份远过于理智,主观的成份远过于客观。坦白的说,我对净土的看法大部份都是受了个人的经验和心情所左右的;因此说出来的话,私见的成份很重,学术的成份极少,这是先要向读者声明的。经过几乎半世纪的“学佛”生涯,回顾以往,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惆怅。我的感想是:在菩提道上努力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得到成佛作祖的成就,又有几人呢?无论你如何努力,但限于天分及共业,今天你在菩提道上所能得到的成就多半是极有限的。这种学道不成的苦痛实百千倍于世事之挫败,亦惟有亲身经历者才能深知其痛的。其实,一个人是否能在“道”上有成就,大概皆是命中早就注定了吧!白居易有诗云:
“人生何所欲,所欲惟两端,中人爱富贵,高士慕神仙,神仙需有籍,富贵亦在天……”
所以一个是否能“成仙得道”,要看你是否生而有“籍”而定了。原来求道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此自古皆然,亦何足怪?在世事上失败了的人,可以在佛法中找到希望和慰藉;但是,在佛法中失败了的人,却又如之何呢?幸亏有一个净土宗,因为任何人都能在净土宗里找到他最后的希望和凭仗!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人生的终极问题决不是人的智识或任何努力所能解决的。这一个无可奈何的悲哀,在学佛的人来说,会冲淡许多,也许只有一点薄薄的影子。这一些薄哀,有时也会在法乐和佛力的加持中融化净尽,诚心念佛的人,我想至少都有这种受用吧!
不谈成佛作祖,不谈往生极乐,不谈念佛三昧,仅凭一股信心和不断的努力念佛,就能在现世中得到佛力加被下所产生的祥和、安全和悦乐感。自己切切实实的感到时常在佛力的笼罩及护导之下,人生的一切困难和苦恼都能获得适当的解决,这样的收获还不值得吾人努力去争取吗?
现代人对死后往生之说可以抱怀疑的态度;但是,修净土的人现世就能得到广大利益的事实却自古皆然,如今亦在在皆是,我想这是任何公正的人所难以否认的。因此,即使站在现世的立场来讨论净土宗,其宗教价值亦巍巍大观,难可忽视的。
站在佛教的立场来看,净土宗的重要性在多方面都超过其他各宗,因为它是一个浅显、易行,不论禀赋环境和教育程度,人人皆能行持的教法。
大乘佛法中,能实际派上用场,可以实际起修的宗派实在不多。历史证明只有禅、密、净三宗能开花结果。但禅宗和密宗都需要过人的禀赋才行,明师、机缘和充足的福慧资粮准备,缺一不可,所以皆是“难行道”,而不是像净土般的“易行道”。大乘正轨的菩萨道亦是难行道而不是易行道。就迫切的宗教需要来看,人命在呼吸间,随时可死,没有得到生死自在和明知去处的人,对死亡之一关,云何处理?此心云何安排?有大勇气大担当的菩萨们可以不惧娑婆之恶浊和痛苦,乘愿再来,为众生服务。对这种人来说,当然也没有什么需要安排的,一切乘愿而已。但身受娑婆种种极苦,深知自己“受不了”和“不够格”的人,则必须要安排一个去处,对这些人来说,哪里还有比净土宗更好的呢?在过去的农业社会中,能行通“难行道”的人都十分稀少,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紧张、忙迫的工业社会中,除了净土的“易行道”尚能为多数人实修外,其他大乘的各种“难行道”岂非比以往更是难上加难么?有勇气有根基的人不应当舍弃菩萨之“难行道”,因为那是佛法的根本,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净土之方便易行道才是实际能派上用场的。
净土宗的基本贡献,我想有四个重点:
- (一)对人生之去处及归宿提出了回归净土的明确指示。
- (二)在宗教的修持上,提出了“依佛力”和“自他共愿力”的教法。
- (三)以“易行道”来解决一切宗教问题,不依显密二教之常轨,因此摆脱了种种困难,以方便道而直超觉地。
- (四)生前修大乘悲智之教为众生服条,死后则期生净土,伴上圣学而究竟菩提,因此是一个现、未皆能圆满的教法。
以上对净土宗作了一些不成系统的漫言,现在让我们来读一读净土宗的三个根本典籍,即: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为了便利读者能较容易的吸取此三经之要点,此处未载三经之原文,只节录了一些原经之精要处。这种把印度繁复文学体裁之经文予以选节,对现代人来说应该是有便利和实用的效果。节录此三经的目的是:希望以此七千字左右的节文就能把净土宗的三个根本经典之要点介绍出来。这个构想可能是期望太高了,但凡事总有个开始。不朝这方面去努力,大乘经典越来越没有人去看了。节选阿弥陀经时,同时采用了罗什及玄奘两种译本,但见仁见智,各人不同,我的这个三经节要,未必就是最恰当的,所以读者如果想知道更详尽的内容,仍应参阅原典,又,因为观无量寿经中所说的十六种观法(其实只有十三种,其他三种则是讲诸品往生的。)实在太复杂,很难修持,古来能够圆满修持此十六观的人恐亦为数不多。后来修净土的人则大都用持名号或念佛的方法,而不用观想式的念佛方法,足见十六观的修法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是太为繁难了。因此只摘录了三个观法,即:日轮观(第一)、佛像观(第八)和往生观(第十二)。
现在的这个净土三经节要,我想还可以再加选节,但为了使初学的读者知晓原经之大概,所以没有选节太多,进一步的选节只有待诸异日了。
(二)净土三经节要
一、阿弥陀经节要(大正366、367,P.346-351)张澄基 节录 二、无量寿经节要(大正360,P.265-279)三、观无量寿经节要(大正365,P.340)
(三)净土泛论
阿弥陀经在净土三经中最短,全文不过二千字左右,但亦因其简短,所以流传亦最广,经文的纲要大概有下列几点:
- (一)此经是佛自己主动的说法,不是像平常一般的被弟子劝请后才说法,显示出其特殊之重要性。
- (二)说明西方净土之概况及往生净土之方法。
- (三)十方诸佛赞叹此经之不思议功德。
- (四)诸佛赞叹释迦牟尼能于五浊恶世成等正觉及说此难信之法。
排于经文之最末段之第四点实最值得我们注意。就佛的立场来说,当然是先要说明主题--净土之道:然后再附带的说诸佛赞扬释迦能于五浊恶世成佛之难能希有。但是就我们众生的立场来看,此最末一段实最为紧要,因为它是净土法门的亲因,因为,一、若无释迦在这个世界上成道就不会有人知道此净土法门。二、若无五浊恶世之种种苦痛,人们也生不起真实的厌离心去求往生,对五浊之恶若无深切的认识,没有经过切肤之痛的人怎样生得起出离心呢?过去诸贤对五浊恶世的解释,今天看来好像已经不够味道了。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恶和浊实空前未有,恶浊的广度和深度已经到了极处,非前人所能梦想,我虽躬逢其盛,但拙于文笔亦难描绘其万一也。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无论用什么方式去欺骗去矫饰也掩盖不住它的种种恶浊。没有过错的人也随着受苦遭殃,整个的时空都充满了灾难与不幸,所以叫做劫浊。
思想混乱,价值破产,百千邪说惑人眼目,谁不惶惑?谁不迷失?一人之误万人火坑,这是真正空前未有的见浊。
今世之所谓文明,所谓进化,无非增长种种贪瞋疾病,作茧自缚,为彼奴役故名烦恼浊。
此身脆弱众病所缠,饶汝志比天高奈何薄命前定,有此时缺了彼,有这时又缺了那,总是差了一点,迟了一着,人生恨事罄竹难书,是名命浊。
你浊我浊,东浊西浊,前浊后亦浊,人畜兽禽无一不浊,秽气所播,鬼神亦浊,故名众生浊。
这样恶浊的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泥?还不想到弥陀净土去求个歇处么?
阿弥陀经中有一句话,对我个人言,有极深钜的影响:
“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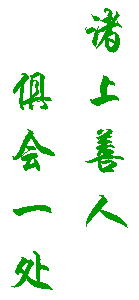
在娑婆世界学佛,其困难实在是一言难尽,许多问题自己都没法解决也无人请问,这种苦痛若非亲身经历是难以想像的。弥陀净土中尽是一生补处的十地菩萨,与这些上圣俱会一处随时请问法益岂不大妙?这些大菩萨中又以观音为最,如果能与他谈论更深一层的般若理趣,求他开示其百千悲智秘行之经过,请他解释古今中外许多难可解了的业报因缘,岂非人生之至乐乎?大乘某经中曾悬记龙树菩萨圆寂后当生西方极乐国,若能与他当面谈谈中观,一何快哉!向令人景仰的慧远、永明、善导诸大士请益法要,其乐又何如哉!
往生弥陀净土,还有一个最吸引人的好处,那就是可以经常以神力到十方世界去参礼诸佛圣贤,奘译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云:
“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土中,昼夜六时常雨种种上妙天华,光泽香洁,细软杂色……彼有情类……每晨朝时持此天华于一食顷飞至他方无量世界供养百千俱胝诸佛……”
这样看来,所谓往生西方净土,实际上等于往游十方百千万亿刹土,任何地方都可以去,不仅限于彼土一处了。对我个人来说,这就可以有机会到东方不动如来处去朝礼尊者密勒日巴,去看看惹琼巴了。还有那些令人怀慕的佛教英雄们,如罗什、玄奘、达摩、慧能、道一、从念、杜顺、法藏、冈波巴、莲花生、米居多杰、龙清让蒋……诸大士,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都有机会见到了!天地间那有比这更具吸引力的事呢?
净土三经中所说之教法虽然很多,但其心髓我想仍在一个“愿”字。此又包括佛的本愿和我们的意愿,此二愿合和才有净土戏剧的产生。因为有弥陀因地之四十八愿,才有西方净土之形成,因吾人有至诚哀慕求生净土之心愿才能有往生之事实。净土生无生论中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况无量寿佛因中所发四十八愿誓取极乐,摄受有情。今道果久成,僧腊久满,故凡百众生勿忧佛不来应,但当深信忆念数数发愿,愿生西方,如磁石与针任运吸取,然磁能吸铁而不能吸铜,针能和磁而不能合玉,譬如佛能度有缘而不能度无缘,众生易感弥陀而不易感他佛,岂非生佛誓愿相关者乎?”
弥陀在因地所发之四十八愿如像磁石,吾人诚愿往生则如像铁针,二者有一种自然和合,自然相应,自然吸取之势,净土教法之基本原理实不出此二愿和合之理。这又十分像宗教现象中之“神人相吸”之普遍原理一样,神必须向下入世来普度众生,众生则必须向上出世投入神的怀抱,如此上下相交如磁之吸铁,正是易经泰卦所明阴阳倒置才能天地相交,才有宗教现象产生之道理一样。但磁能吸铁而不能吸铜,娑婆世界之众生与弥陀和观音容易发生感应,与其他诸佛则不尽然。净土虽有多种,如不动佛净土,药师佛净土或弥勒内院等等,但这些净土的因缘好像都不如弥陀净土来的亲切和普遍。大乘经典中劝导学人回向弥陀净土之处也远比其他为多,这强力的说明了弥陀和观音与吾人之因缘实较其他诸佛更为亲切。
弥陀因地之愿力与吾人诚心往生之愿力相应和合则能产生往生之事实,这样说来往生净土是否仅凭诚挚的愿心一个条件就够了呢?除了“愿”之外,是否必须修广大善行,发菩提心,达成一心不乱或念佛三昧等等才能往生呢?这些条件都是经中所说,如欲达成高度的往生当然是需要的,但就最低的水准说就不一定了。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之第十八愿说:
“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
该经又说:
“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唯除五逆诽谤正法。”
任何人只要对阿弥陀佛至心信乐想念十次(或是一次)佛像,或称念十次甚至一次佛号即能往生了。犯了五逆重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恶心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及存心破坏毁谤佛法的人毕竟不多,因此任何人只要至心信乐稍为念点佛就可以有最低的往生条件了。这里并没有说必须要发大菩提心,修广大善行,得念佛三昧或一心不乱的种种条件。因此,弥陀因地誓愿之无边威力在这一条愿上充分的显示了出来。此处强调依他力而得度的方便,实明显至极。观无量寿经则更进一步说:
“若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是愚人以恶业故,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此愚人临命终时遇善知识种种安慰,为说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惶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归命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
依此,则即使作了五逆十恶的人仍旧可以往生,任何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步,只要回心向善还是有希望的。悲愿至极的弥陀亦理应如是才能使人觉得真正的大悲佛陀,其宏愿是应该这样无机不摄的!但为了避免使人误会作五逆十恶的人也容易往生,所以加了一个条件:在临终时要遇善知识教使念佛才能往生,这种机缘就不一定容易遇到了。这种说法的方式实在是煞费苦心!细思净土三经对往生净土的条件之说法颇不一致。一会儿说“不可以少福德因缘往生彼国”,一会儿又说一念即可往生,往生的条件有的说得很难,如念佛三昧,一心不乱,发大菩提心修广大善行等;有的则说的很容易如十念佛名亦可往生,这究竟应该如何解说呢?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即:从佛的立场去设想。佛陀说法实在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一面要鼓励人向上向善;一面又要强调依佛陀本愿之悲力人人皆得往生。太加强向上向善的条件则容易使人生畏而怯步,太加强他力及易行道,又恐人轻心放逸舍弃善行,因此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为了使道理上无矛盾又推出上、中、下三品往生之说,实在是煞费苦心!我个人的信念则是:“只要二愿相感如磁与铁就必定能够往生的。佛的悲愿早已圆满不必顾虑,只要我们自己的愿心诚挚强烈就必定能往生,所以时时念佛,时时赞祷,此心常念弥陀和净土,经常与弥陀打上交道,累月经年下来自然能够培养出强烈诚挚的意愿的。这不但是因为二愿契合的法尔道理,还有万法唯心的原故,因为一切外境和因缘无非自心所变现,所以强烈的心愿加上巧妙的时机(前业已尽,后业未生的临终刹那),再加上佛心与自心相摄相感的力量就自然能够冲破障碍往生净土了。因此我想往生净土与否的关键在自己是否“至心信乐”和有无强烈的意愿而定。
细读第十八愿就知道,要至心信乐的人才能十念往生,十念很容易,只需片刻,但至心信乐就不太容易了。真诚恳切的愿心必须至心信乐才能生起的,这并不是普普通通皮皮吊吊的愿心,而是一股至诚和深入的强烈愿心。至诚就必须有那专一、忘我,和全体投献的心理状态;深入则意味着三种不同的深入:了解的深入,感情的深入和意愿的深入。了解的深入是深深了解在一切法门中惟有净土是最殊胜的,对自己言也是最合适的。意愿的深入是一种迫切渴望往生之情远超过对此世一切之愿望。感情的深入就比较难讲了。一般说来,师徒、朋友、夫妇、眷属等之间的深厚感情并非是一日得来的,乃是经过长时的接触和交往以后逐渐培养起来的。如果连交往和熟念都没有建立起来那里谈得上感情呢?同样的道理,我们和弥陀之间如果连接触和交往都没有,怎样发得起“至心信乐”的感情呢?言此至,想起多年前一个百老汇的歌剧: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剧中的主角是一个犹太族的老农,他信教虔诚,昼夜六时的生活起居中无时无刻不和上帝打成一片。早上起来,如果看见天气很好他就对上帝说:“谢谢你啊!这样好的天气赶到集上去一定可以多买一点乳酪了!”碰到不如意的事或遭到无故的欺凌时,他就对上帝说:“你看哟!为什么你这样粗心大意不照顾我呢?”他常常独自与上帝说话,向他吐诉心中的一切快乐或哀愁。最令人感动的是,是他的心境中上帝已经不是一个遥遥在上高不可及的神,而是一个切身的伴侣了,他对上帝说话时已经不用“神”字来称呼,而直接说“你”要怎样怎样了。这种“你--我”直接相对的心理状态,在宗教学上有很重要的意义,下面再谈。这老农对他的神早已超过了至心信乐的阶段而是片刻不离,相依为命的关系了。心境到了这种状态,深心、愿心和信乐心还有什么问题呢?所以说生起诚挚强烈的愿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先能做到“身心全体交付”,再加上长时的培养熏习才能达成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心不乱和念佛三昧除了使自己的心境能与佛境发生相应之处,其另一主要的作用还是要使自己能够达到“至诚”和“深愿”的境地。
回到本题:究竟要有怎样的条件才能往生净土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古今大贤解说不一,佛经本身的说法也差异很大;从很严格的发菩提心,般舟三昧,一心不乱,广植众德,至心回向等等到十念或一念即可往生。从中国正统净土宗之鼓励出家素食到日本亲鸾上人的全仗他力,在家茹荤,其间之差异实非常之大!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则又有另一说法:
“又复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皆悉散坏,一切亲属皆悉远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到已即见阿弥陀佛……”
这是很明显的说,只要发菩提心,不舍菩萨之广大行愿就可往生,连念佛三昧,一心不乱,甚至称念佛名等都不是必须要的了!以上这些差异的说法,稍加思索就知道并不是互相矛盾,而是说法之不得已处或方便善巧处!佛陀鉴于众生根性不一,其所需之教法自然亦不相同,所以必须“方便多门”的设施种种差别法,所以其立教精神是随顺众生的。其他宗教则是以神所见到的一个“真理”或一个“道”硬性的交给众生,必须全盘的接受,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再者,世界上大多数的宗教都是采循“非此即彼”(either……or)的路子的;不是我们神说的法就是魔说……不信吾教的人就永不能得救的。但佛法则是相信“亦此亦彼”(both……and)的原则的:这样去修可以得道,那样去修也可以得道。前者是神本、权威、非此即彼的独裁式;后者则是人本、包容、亦此亦彼的民主式。因为方便多门,弹性很大,所以佛教这种民主色彩极浓的宗教,在短时和当前的问题上说是显得迟缓乏力,黑白分明的答案也不易很快的找到。像我们现在亲眼见到的多元之民主制度一样,其程序和功能都非常迂回和曲折,其代价亦颇为昂贵,实行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此亦是民主及佛教之特点及可贵处。进一步言,我想佛的关切只有一个,那就是“利他之关切”。这种“利他之关切”是与“神意关切”大不相同的;神意的关切是说,神的最大关切是要把他自己认以为是的道理作为教法,来晓谕众生,甚至不惜用强迫式的方式来灌输给众生,其基本性质是要众生来随顺神的意旨。佛教的利他关切则恰恰相反,是以众生的根性、利益和需要为前提而方便施设法要,其精神是随顺众生的。这就是说,在某一时空内适合一类众生所需之法,佛即以种种方便用不同的姿态而施与之,如果时间和环境变了,说法的方式亦必须加以修正或改变,除胜义谛的道理如空性、佛性、唯心等万古常恒之理不可改变外,其他的教法则随众生机,应众生需而行各种方便的适应。“佛无定法可说”之义亦可作如是会。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我们就可以解答许多净土宗教之质难了。美国大学生学到净土宗的课程时,通常都有下列的疑问:
(一)净土经中所描写的极乐情况,例如黄金为地,宝树宝池、天乐法音等等,今天我们看来并没有什么可乐之处呀?如果遍地都是黄金和七宝则毫不稀奇,无甚价值了。再者,黄金的大地那有绿茵的草原来的可爱呢?七宝行树也没有天然的树木和花草清新宜人呀!
(二)四十八愿中之第二十一愿:“设我得佛,国中人天不悉成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觉。”第三十五愿:“设我得佛,十方……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乐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寿终之后复为女像者,不取正觉。”这两个愿充分主张“男性优越论”蔑视女人实在不应该。
(三)净土中人皆是三十二大丈夫相,当然都是男人,具足男根,但净土中无女人,这不但在生物学上讲不通,在哲学的目的论上亦很难自圆其说,如果没有女人则男相究竟有何用处?有何意义呢?
解答这三个问题之前,我想首先提醒读者,有关佛教圣贤说法之几项原则:
- (一)佛无定法可说,是应众生机,随众生需而施设法教的。
- (二)因施教之原则在“随顺众生”,故随环境及需要而施设种种权巧方便之说。
- (三)某一方便之效果发挥尽致后,必然会演进至衰敝之阶段而丧失其原始作用,此时则必须有新的解释来激发再生之作用,新的方便于焉产生。
- (四)佛之境界非人类所能臆测,佛必须要牺牲其全体,无限及深邃无涯之广大见解来将就人之有限愚蒙意识。佛必须要顺众生心,顺众生业,顺众生机,顺众生执来说法,这样,所说之法就必然会受到种种限制和有所偏向,不能将真理之全体显露出来,此为佛教圣贤之苦衷及其不得已处,吾人在批评佛法时,应常常牢记此点。
基于以上四点认识,我们对现代人所提出之种种质难,就可以作较公正的解答了。
净土三经中,所描写的极乐情况,乃对当时印度人所憧憬之“极乐”而来。黄金、七宝、天华、妙香、八功德水这一套皆印度人所极端喜爱者。因为随顺听众之喜爱所以讲了一大堆他们理想中的极乐和妙宝。遍地黄金和到处七宝今天我们看来诚然有“略嫌俗气”的感觉,远不及富有自然生命的青树、绿草、鲜花来得清丽宜人。但不要忘记,往生西方的人,他们感觉及审美的官能是不是和我们一样呢?他们所见到的七宝、栏杆、香华等与我们的黄金、七宝可能完全是两回事!焉知他们的黄金和七宝等不是宇宙美妙之极品,亦能生起无尽之生命活力及美感呢?其实黄金、玛瑙、砗磲……这一套名词只是形容其贵重及美妙而已,岂能硬指人间之实物?!极乐世界之瑰丽庄严难可思议不易形容,经中一再说之,如第二十七愿说:
“设我得佛,国中人天,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逮得天眼,有能名了辨其数者,不取正觉。”
第三十二愿云:
“设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流华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严饰奇妙超诸天人。”
局于语言及境界之限制,说法人很难对听法人清楚的形容净土之美和乐。我们的境界与净土的境界毕竟是不相称的,难以比拟的(incommensurable),因此经中对净土之美和乐的描述,只有用一种权巧的,不得已的描述,挂一漏万自是难免,所以我们读净土三经时宜活读而不宜死读。
关于净土之“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宝树、宝池、天乐,妙香那一套。净土中真正的“乐”乃是法乐而非声色之乐。法乐除了由听闻法要而产生之悦乐外,还有一个更深入的超越世间一切喜乐之“极乐”,此即第三十九愿所明者:
“设我得佛,国中人天所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
漏尽比丘所享之乐,乃证入涅槃性所生起之解脱妙乐,其乐超绝言思及分别境界,乃原始佛教所追寻之目标,具有宗教之究极价值及意义,这一点常被学人所忽略了。
关于第二个质难:净土中尽是三十二大丈夫相及厌弃女身等,亦是因当时印度之社会及习俗环境而起。人类的社会一向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固不论其道德是非究竟如何,男性中心为人类历史之主流实为不争之事实,在男性中心之社会中,女性所受之欺凌及歧视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深观世法皆苦的佛教当然不会忽略此极为普遍的大痛苦。因此,“女身”就成为必须要解脱的对象。我想佛陀如果对一九八0年代的美国人说法就不会采用这种方式了。再者,许多大乘佛经都一反原始佛教的传统看法,极力赞扬女人,女人刹那成佛的例子,及女胜于男的故事到处皆是,在密宗里,女性之地位更是优越,几乎有超胜男性的趋势。
至于净土中人皆是具有三十二相的男子,我想亦无非是说大家皆形貌端正而已,三十二相是印度美男子的典型,于是就这样套用上了。其实,在思想上更有意义的是第三和第四愿,第三愿说:“国中人天,悉皆金色。”这是没有种族和色类的差别,大家一律平等,因此,净土中就绝不会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第四愿则进一步说:大家的形色相同没有好丑,因此消除了许多不快和烦恼之因。根据此二愿去推理,净土中人应该是无男女相的,魏译无量寿经卷上(大正360.P.271)明显的说:
“其诸声闻菩萨人天,智慧高明,神通洞达,咸同一类形无异状。但因顺馀方故有人天之名,颜貌端正超世希有,容色微妙,非天非人,皆受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
无量寿经第十愿说:
“设我得佛,国中人天,若起想念贪计身者,不取正觉”。
这更说明了其国中人对身体根本无贪计之想念,身体的事情连想都不想它,还有什么贪执、分别、男相、女相呢?
我们如果抛弃一切传统的成见,用客观谅解的眼光来检讨净土三经对极乐世界的描写,就可清楚的看出说法人只是想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修行的好处所而已。那儿具足各种便利修行的优胜条件,而没有任何人间的违缘和障碍,是一个安稳舒逸的理想修行道场。例如:男女色欲为众苦之源;为修行之主要障碍困扰,因此就说极乐世界中没有女人(这样当然所谓的男相亦失去意义了)。娑婆世界的众生,为了衣食终日辛苦互相残害,因此就说极乐世界中衣食随念而至。娑婆世界中,求法不易,入道无门,因此极乐世界中的树木花草都时时在流布法音,“国中菩萨,随其志愿所欲闻法自然得闻。”娑婆世界中邪师和庸师满天飞,到处误人,所以极乐国中尽是大德圣贤,还有许多一生补处菩萨可以时常亲近往来。娑婆世界的众生为了钱财争斗抢杀,因此极乐世界到处是黄金和七宝,财宝因此失去了争抢的价值。娑婆世界的众生限于业力其行动非常不自由,所接触的教法及宇宙亦极其有限和渺小,因此极乐国的众生就有“于一念顷能遍游十方世界,朝礼十方诸佛的神通和便利……”
这样把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两相对比,就知道净土的德相都是针对着我们的缺憾和苦痛来说的,只要能把握这个大原则,吾人就能够了解佛陀说法之苦衷,不必死执文句去斤斤较量其他细目了。
还有一个小问题,此处应顺便一提,东西南北之方向乃根据地球绕日或依北极为定准而来,这种定向的准则亦是相对的,美国到底在中国之东边或西边都可以说得通,太空中更难肯定一个绝对的“东、西、南、北”,因此西方极乐世界的“西方”二字,又是一种顺众生心和顺众生执的方便说。但是,宗教行持又不能没有一定之准向,因此就标唱西方,这样才能使众生心有所专。西方又是落日的方向,象征着休息和归宿,看看西方的落日使人有一种歇处和归处的感觉。在痛苦的娑婆挣扎了一辈子,看见落日自然就会生起游子归去的感怀,这也是标唱西方的另一主要原因吧!
(四)念佛三阶
无论是观想佛之相好或念诵佛之名号,或二者兼修,此处一律称之为念佛,抛开宗教的意义不谈,就纯瑜伽的眼光来看,念佛亦是一种非常善巧的修习定慧之法门,所以应该称之为念佛禅。由念佛而得加持,专注及种种相应,因而进入三昧及胜义智觉之境,此一历程经过之详细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对专修者来说尤其重要。但是,关于念佛禅之次第境界必须要有经验的人--那些修习念佛禅几十年以上的人,才能如数家珍,谈得贴实入微的。这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严格的说,我是决不够资格来讨论的。所以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应该和在这方面下过苦功的老参们请益,及参阅有关方面的书籍。此处我只想根据宗教学上之某些基本原理,对念佛之次第境界作一大略之陈述。
近代犹太教大哲马丁布白氏(Martin Buber)所著“I and Thou”,我/你一书,在宗教学上极具价值,为人称道。从佛学的观点来看,此书虽亦觉得不错,但总嫌有点不够深邃及究竟,错误及偏见之处亦很难免。格于犹太教义之神人二元论之先天思想,布氏不能作进一步之突破而进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境界,十分可惜。但他的见解在宗教学上仍是颇有价值的。布氏把人的心意活动分成两个境界或领域,一个是(I-It)我/他的境界;一个则是“I-Thou”我/你的境界。前者略似佛家之比量,后者略似现量。我/他(I-It)的境界是指意识缘想各种事物,把事物当做一种所缘(object),一种与自己不相关联的所缘物品。例如:“李忠的头发是灰褐色的,眼情也有点发青,嘴唇厚而翻,有点儿像非洲士人似的,右肩好像也有点歪。他虽然头脑清楚,办事敏捷,但用他做公共关系的代理人,毕竟是不合适的,还是另找别人吧!”这一连串思想中所用的名词,如:李忠、头发、灰色、嘴唇、右肩、代理人等等,都是意识中所缘想的某种事物。这些心意所缘之各种物品(objects)用代名词来说,都是一种他或它(It);所以这种心理状态布氏一律归诸为“I-It”我--他,或我/他领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份时间都是在这种我/他的领域中度过的。至于“I-Thou”,我--你或我/你的境界就大不相同了。当我们对某人愤怒已极,脑中一片空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什么思想意念都生不起的时候,我们会拼尽全身的力气,睁着大大的眼睛,瞪着某人大吼一声道:“你!”说这个你字时,我们是用整个的生命(our whole being)来说的,不杂任何意念思维,是一种当下、现前、真挚的情况。说“你”时,此你字之性质并非代表意识所缘之某种物品(objects),而是我--你之间的某种纯粹关系。说“你”时,当然意味着我--你的关系,说“他”时,当然也意味着我--他的交涉。但二者的不同是,说“他”时,“他”代表一种与自己相隔离的某种物品。“他”是我所缘想,我所欣赏,我所把玩,我所操纵、喜厌、取舍……的某种物品。说他时,也不必用整个的生命去说,只要用意识去说去想就行了;也不必是当下的现量。其实,凡是我/他的领域,大半都是属于过去的,而不是现在的或当下的。但说“你”时,就一定是现量的当下,而决不是过去。此时我与你之间只有一种纯粹的,不可分开的关系存在,而没有“思”及“被思”的架构存在。因此,我/他的境界一定意味着某种分离或隔离,而我/你之境界则意味着某种纯粹之结合。
上面在解释“I-Thou”我/你之心理领域时,只引用了愤怒时之情况。其实,其他的例子甚多。凡是吾人用全部的生命,真挚的把整个的“我”抛向对方的“你”时,此我/你的境界就产生了。母亲痴痴的望着她那将要死去的儿子,哀痛的泣道:“你!你!你啊!……”在极端绝望,极端惊异,极端欢乐,极端魂销的情况下,那不由自主,所呼唤出来的“你!你!”皆是“I-Thou”境界的表现。
我/你的境界一定是亡言绝相的。这种没有语言的我/你境界,最好的例子的是婴儿。婴儿初生不久,脑中没有语言,也没有思想,所以根本没有我/他境界之可能。婴儿与外界的接触,主要的是靠他那两个微微向内卷曲的小手;大人的手去摸他时,那两个卷曲的小手就会很自然的,很灵巧的紧紧抓住这外来的手,这是婴儿整个的生命与外界之纯粹接触,是当下的、现量的、真纯的、这是一个蒙眬的“我”用整个的生命去找寻那个可触及的“你”,其中不杂一念,所以是一种纯粹的我/你结合境界。
在我/他的领域中,此心是异常活溜捉摸不定的,它是会耍弄各种计巧、欺骗和操纵的手段的。但是在我/你的领域中,就不能如此,因为我/你的境界一定是纯真的和直心的。欺骗和玩弄都是意识在捣鬼,我/你境界中既无意思分别,怎能有欺骗或曲心之可能呢?站在西方宗教的立场来说,人与神之间之真正碰面(confrontation)。一定是我/你的境界,天国亦必定是这种纯真的我/你境界。“I-Thou”之主要宗教意义大概在此。
以上所谈的我/他及我/你二重境界其实是不完全的,宗教的领域也绝不止此,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场来说,最少应有三重境界:
1.I-It 我与他的境界 2.I-Thou 我与你的境界 3.I-All 我与一切的境界
布白氏把意识分别的我/他境界之价值贬责太过,且硬生生的认为我/他和我/你的境界是不可调和不可相通的。这又是西洋思想家的自性执在作怪。佛学的看法则是应该把意识和无意识(或阿赖耶识)之间的鸿沟想法子除掉;使意识和无意识融化成一体,这样才能达成无分别智--那无有意识分别的智慧,这样就能超越我/他和我/你的二分领域而进入“我与一切”的同体境界了。
我/他,我/你,我/一切,之三步境界,用最通俗的例子来说,就像是一个主妇在学着做一道新菜;第一步她要找一个好的食谱,或向内行人请教如何去找最适当的材料;时间、火候、和酌料等等应该怎样处理……这一切都是属于意识的资料问题。烹调方法之内容皆意识所欲知之对象(objects)。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一种我/他(或我/它)的关系。等到菜已经做好了,端上桌子当下现成,眼观其色,鼻嗅其昧,就成为一种直接的我/你相对的关系。捡菜入口,大嚼享受,吞入腹中,菜就进入自身化成一体,我/你的关系亦全部消融,成为自他一味之(I-All)我与一切之关系了。
这个例子也许不是最恰当的,因为宗教境界毕竟是与此相差太大了,用我/他,我/你,我/一切三个范畴来解释念佛禅的次第境界,可简述如下:
一个人在开始经常念佛的时候,他心中自然会对阿弥陀佛和净土已经有了若干的认识,因为这样,他才能生起意乐,发生向往之情去诚心念佛。在这个阶段中,严格的说,他对阿弥陀佛只有某些抽象的观念而已,谈不上任何实质的接触。例如:知道阿弥陀是无量光或无量寿的意思,在因地时名法藏比丘,曾经发了四十八宏愿而成就庄严净土。净土中无一切苦恼,有各种庄严、法音和法喜时时充满……有二大菩萨观世音和大势至常侍阿弥陀佛之左右,助彼宏化……这些观念都只是属于知识的范围,乃吾人意识中之若干资料而已。
我们从佛经上看到有关弥陀和净土的描述,脑海中就有了若干印象。尽管我们心中说阿弥陀佛是大智大悲大力的圆满佛陀,悲愿宏伟,与吾人因缘至深,但这一套观念仍脱离不了我/他的范围。阿弥陀佛仍不过是吾人心中的某些观念而已。如果我们与阿弥陀佛的关系仅只于此,那就实在没有太大意义了。净土三经对阿弥陀佛的描述,老实说是非常贫乏的,经文自己也说百千劫亦难尽述弥陀之德相和净土之庄严。我们读了净土三经后,心中能不能生起一个活生生的弥陀画相呢?净土三经对弥陀和净土的描述,就文学逼真的意味来说,赶得上西游记上的孙悟空吗?赶得上“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尔和娜他夏吗?小五义中的白眉毛徐良好像要活神活现得多呀!仅靠净土三经的描述,我们对阿弥陀佛毕竟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心中能生起一个清楚、生动、活栩栩的阿弥陀佛吗?答案是:净土三经是宗教文献而不是文学著作。如果一定要把它当作文学作品,那就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因为著者的目的不是要详尽的去描绘净土和弥陀之相状,而是想透过宗教的语言来诱导读者去实际修行和念佛,由实际的修行就能亲自见到弥陀和净土,就能超越观念的领域而直趋现量之觉地。这样由比量进入现量,由我/他之境界进去我/你之境界,这种亲验的直接证境不是比千言万语的文字描写要强得多么?
念佛未入门时,脑中只是充满了一些关于弥陀的观念,尚不能与弥陀发生直接的接触,阿弥陀佛充其量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他”;与自己的关系好比是皇帝与庶民;皇帝是神圣的,权威的,保佑庶民的,但也是遥远的,庶民对皇帝无论如何尊敬爱戴,也不能发生真正亲密的关系。臣民对皇帝要称陛下,称皇上或天子,但决不敢称作“你”。对皇亲贵族说活都要用第三人称,如太子、太后、娘娘等,也决不能直接说:“你怎样怎样。”对尊敬的人说“你”,就自然会觉得是一种大不敬了。人类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对自己所尊敬或最崇拜的人或神,一定要把他供得高高在上、遥不可及,这样才能增加其崇高性、权威性和神秘性。但这样也就拉远了神人之间的距离,不能亲切了。前面所说的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中的老农,从早到晚都和上帝直接谈话,时时都用第二人称的“你”来称呼上帝,他这样做,不但丝毫无损于他对上帝的尊敬和爱戴,且能证明他的宗教素养已经进入了真挚现量的我/你境地,他已经不再讨论关于神的事,因为他已经直接与神谈话了。(He no more talks about God,but he talks to God.)这才是真率的,纯朴的我/你境界。杜甫的醉诗歌中有句云:“忘形道尔汝,痛饮真吾师!”一个人要忘了形--忘了一切伪装,忘了意识的我,才能够道尔,汝!足见那纯真的我全体投向纯真的你时,才能有我/你境界的出现。
近代日本净土真宗有一个名叫Shoma(正米?)(1799-1871)的信徒,他是十九世纪的人,所以老一辈的佛教徒对他的事迹还记忆犹新。(注13)正米是一个穷苦的佣工。一天,他和友人来到一所乡村的庙宇中,该庙的大殿中,供的是阿弥陀佛,他一走进弥陀殿,就站在佛龛前伸了一个大懒腰,立刻就倒在地上伸开两脚大睡起来。与他同行的友人看见他这样,不禁又骇又恼的说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对佛祖这样是大不敬,成何体统呢?”正米答道:“我已经回到自己父母的家中来了,当然要这样罗!你说这种话全像是个继子或孤儿的口吻啊!”
又一次,正米在稻田中作工,感到十分疲劳,就回到房中坐在窗下休息。此时一阵清风吹来,十分凉爽,他马上就想到了他的阿弥陀佛,立刻走到佛龛前,把供在上面的佛像拿下来,放在窗户前面,对佛像说道:“这股清风实在凉爽,你也和我一起乘乘凉吧!”
又一次,正米从京都回到四国,必须要走一段海程,他们的那条帆船在海中遇到了大风浪,全船的人都骇得要死,大家都拼命的祈祷海神来救命,把阿弥陀佛抛到脑后去了,可是正米却如无事然的船舱中鼾声如雷的大睡起来。等到风浪平静以后,同行的友人们惊魂甫定,就叫醒正米,埋怨的说道:“你这个蠢才哟!这样可怕的风浪,你是怎样睡得着的哟!”正米坐起身来,揉揉眼睛,向四面一望,摸着头皮说道:“怎么?我们还是在娑婆世界中么?”
正米的故事十分感人,对他来讲,弥陀已经不是一个遥遥在上、高不可攀的佛,而是一个朝夕相随的亲切伴侣了。这就是说,在他的心境中,阿弥陀佛已经不再是一个偶像或概念,他早已超越了我/他的领域而进入现量的我/你境界了。不但如此,因为他的绝对信仰已经成就,与弥陀打成了一片,所以心无复任何怖畏。对他来说,往生净土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不假修持,即信即证的法门和境界,实在令人叹赏!我想,这实在是最高最顿最直接最方便的法门了;得净土之神髓者,其亲鸾之真宗乎?
上面所举的例子并不是说修念佛的人,一定要像犹太教的老农或真宗之正米一样。各人的根基和熏陶不同,修行的经验和效果当然亦不一致,但绝大多数的人在修习念佛的初期总难免把佛当作一个高不可攀的偶像、神圣但遥远,超越不了我/他的领域。念佛日久,熏陶日甚,就会觉得自己与佛的距离越来越近。慢慢的,佛已经不是一种意识中的概念或事物(object),而成为一种亲切的当面(presence)了。念佛念得相应时就会觉得有一股加持的力量笼罩全身,心中自然产生难以言说的安详、和平与喜悦;信心、悲心、雀跃心自然增长。有时,自己并没有念佛,在行时、坐时、住时,忽然佛的加持降临了,安详、喜悦之情自然生起。这样的境界虽然很浅,亦略略算得是超出意识和概念的我/他领域,接近现量的境界了。又,念佛相应之时,自然会有“身心柔软”之相;由此“柔软”而能发生轻安喜乐,时时与法相应,渐渐改变气质,甚至由此“柔软”进入松、舍、空的境界而与般若相应。恰如第十六愿云:“十方无量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触其体者,身心柔软超过人天……”诚不我欺也。
佛教行人在超越我/他之领域后,其实亦不必经过如布氏所说之我/你境界,因为佛教之思想及传统与犹太教毕竟不同。佛教行人虽然觉得阿弥陀佛时时都在自己的身边,其加持灵波亦时时浸灌自己,但此时亦不必对佛陀说个“你”字。虽然现量的觉得佛的现前(presence),但并不一定要有面面相对的二元之我/你感觉。佛教的最终目的是与佛陀融合成一而不是犹耶系统的神人相对。由于此一原始思想之差异,在念佛禅的现量觉受上亦会出现很大的不同。虽然如此,我/你境界的若干要素仍是会具备的,例如:当下、现量、原真、离伪、离意识、超语言、诚心、直心等还是一样的。
念佛禅的终极境界决不止于我/你相对之领域,而是要证入我与诸佛同一体“I-All”的境地。此即华严之色空一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境界了。自心之外无佛陀,我心、佛心乃至一切众生心皆互入互摄交融一味,于极无自性之毕竟空中宛然显现无尽法界之种种游戏庄严,极乐净土之终极意趣亦必然如是也。
对净土宗的教义和精神不太熟习的人,往往会认为净土宗的目的是期望超离此娑婆世界到西方净土去享乐,所以仍是一种“逃禅”的态度。如果到西方净土只是为了去享乐,那么我们读读净土三经,西方净土的“纯享乐”究有多大,有多稀奇,就实在很难讲了。由经文看来,西方净土除了法乐之外,其他的乐似乎皆是次要的。经中所标扬的“乐”实是以“法乐”为主的。法乐者,在修习佛法时所产生之乐也。这就是说西方净土是一个理想的修行好处所。环境既好,良师亦多,没有种种困扰和障碍,可以安稳的修行入道。经中处处强调此点,足见其精神是鼓励人到那里去修行,去完成菩提大业,并非是专为享乐而去的。至于“求超离此世界”即是逃禅之说亦是皮相之论。征之事理,惟舍才能有得,惟破才能有成,惟超离才能入妙化,惟出世才能真入世。这都是说:一定先要超越某一范围之外,才能回头来在此范围内得心应手,妙手回春。超离此娑婆世界之作用及意趣亦复如是也。其实净土宗之精神决不仅限于死后往生;生前之善行尤为紧要。观之净土诸贤之生平言行及其对社会及宗教之贡献,决不下于其他任何宗派,抑且过之。此一历史事实堪为净土宗之积极入世精神作证也。有人问印光大师云:“人生观应该如何?”大师回答说:“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心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实在简单明了!入世用儒家的道理,出世则用净土的教法,何尝偏废此当下的世界?今天佛教徒是否应该在入世法上全部采用儒家的说法自然尚有商榷之处;但净土不废入世,且须积极的尽己之力为众生及教法作种种服务,则是净土宗之一贯精神,不容抹煞及忽视者也。
弥陀四十八愿中,至少有十三个愿并不是讲西方净土的,而是针对他方世界众生之利乐而说的。例如:若有人得闻阿弥陀佛之名号则生欢喜信乐修菩萨行(第三十七愿);乃至成佛之间永远不会诸根陋缺(第四十一愿);寿终之后,生尊贵家(四十三);得至不退转地(四十七、四十八);得深总持及无生法忍(三十四);能获清净解脱三昧(四十二)和普等三昧(四十五)……这就是说吾人在生前依阿弥陀佛为本尊,祈赞,称名,一定能得到弥陀的加被,增益信乐及菩萨行;如果在定慧上努力,现世即能获得普等三昧和无生法忍。这就是说,佛法之目标现世即能达成,那有什么消极或“逃禅”的意味呢?以弥陀为依归,生前在娑婆世界作种种二利事业之努力,精勤定慧争取无生法忍,死时则一切交付弥陀,不忘菩萨大悲行愿,期生净土伴上圣学。人生之归趣宁有较此更妥贴更殊胜者乎?搁笔之前,敬告读者应勤修净土,求个心安的归处,这才是人生有意义的事,这才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
智光文字录入 选自 净土专页